中文 In Chinese
-
破碎与修补

一个心烦的、不顺利的秋天写的两篇文章,《破碎与修补》与《野》—— 你知道吗?我是一个由无数个“我”拼凑起来的自己,我每天有十来个瞬间面临分崩离析的可能。我看见过我们家族的女人发疯,看见过美丽的、丑陋的、年轻的、衰老的、婚姻美满的、离异丧偶的、品味良好的、俗不可耐的、为人师表的、道德败坏的女人发疯,这些能量在本质上纯粹而齐一,像是隐蔽幽暗的菌落在泥土里深藏着的长长菌丝,把我们的根系缠绕在一起。 Continue reading
-
三明治,二明治,一明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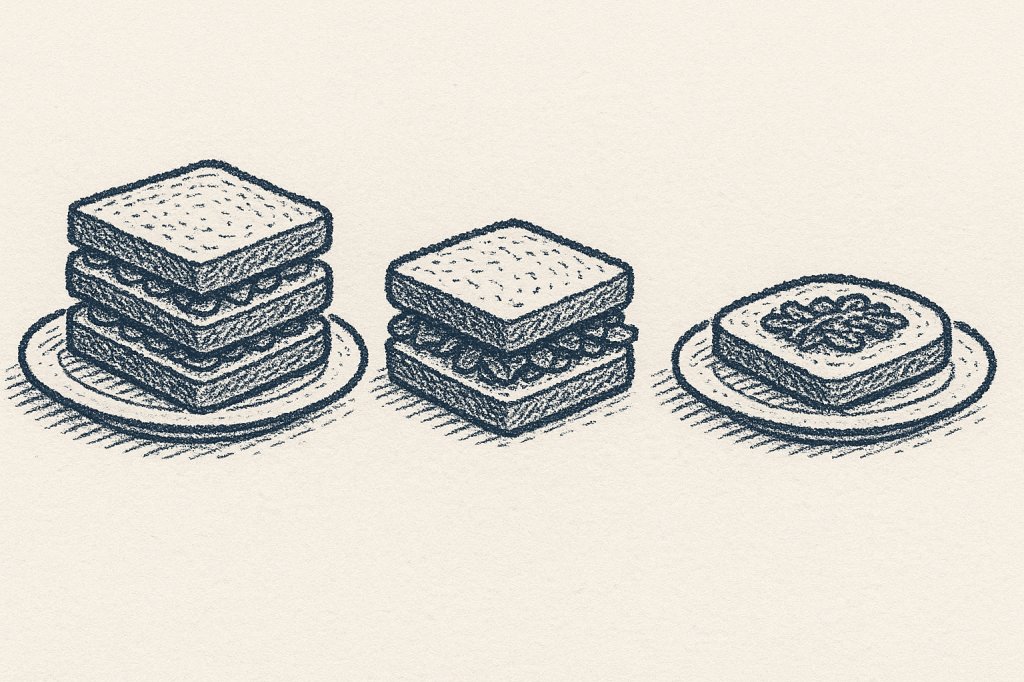
这是一组四篇小文章,都是在今年四月间写成的:《小狗》,《血橙》,《三明治,二明治,一明治》和《他们为什么要吃胡安》。《小狗》是我最近最喜欢的、也是最难过的一篇日记,其实我心底想到的第一个句子便是“小狗尾巴一卷,就是一朵祥云”。 Continue reading
-
伊莎贝拉
我如今在一个寒冷异国(我是喜欢冷空气的)朝朝暮暮地活在我充满教条和宿命意味的“寒逝晓至”的本名下,伊莎贝拉这个名字偶尔会窜上我的心头。我的好朋友Emma住在斯德哥尔摩,他们一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人依然习惯于喊我“伊莎贝拉”。我去年被邀请去她家过复活节,中午在厨房忙活,她的妈妈突然问我:“伊莎贝拉,现在厨房里就我们俩,像妈妈跟女儿一样,你回答我,你活得幸福吗?”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眼眶湿润,我想了一想:“或许我对‘幸福’有很高的定义,我只能说当下是满足的,但很难说‘我是幸福的’。”她说:“那好。如果这样,请你一定不要降低你对幸福的原则。”我曾经真真切切地爱过一个人,这个人讲:“伊莎贝拉是个美丽的名字,但比起伊莎贝拉的疯和小气,我更爱寒晓,她诚然是个天资匮乏、口才迟钝、死气沉沉的书呆子,但她的心真挚、热烈,从不逃避。” Continue reading
-
我更年轻时听的歌
我也许在不同的场合,跟不同的人,轻易而随机地说起过这些。说起这些的时候,就好像,从冬天大衣的口袋里掏出,糖,有些融化了;药,胶囊有些剥落了;有许多彩纸、收据、揉碎的餐巾,也纷纷扬扬一并带出了,散落了。 Continue reading
-
感伤之旅

因为得知外公病重,于是请了两周无薪假,6月15日我回到了成都。受到制裁的影响,欧盟航司的航班都不能经由俄罗斯入境,乌克兰又是禁飞区,赫尔辛基直飞成都的四川航空、直飞重庆的芬兰航空早已取消,经由荷兰、德国、土耳其、中东或香港绕行周转的航班大行其道,动辄几千欧元的票价配二十来个小时的航行时间。从赫尔辛基回成都最快的航班是吉祥航空直飞郑州,再从郑州中转成都;这条航线也是奇怪,仅有赫尔辛基至郑州的去程,没有郑州至赫尔辛基的回程,仅八个多小时就到了。而回赫尔辛基到底要从上海中转。 Continue reading
-
奥兰骑行流水账

芬兰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国家,通常来说:春天去北方滑雪,学校通常会在四月放“滑雪假”,因为白昼渐长,雪还没有融化。夏天短暂而金贵,七月到八月是芬兰最苍翠、温暖的时光,我们一年五周假期,同事往往会在七八月一口气用个三四周,剩下的留到圣诞前后;要么去临湖的夏居,游泳、垂钓、蒸桑拿;要么出海,环游南方的群岛(island hopping);往北边走,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无尽的森林,芬兰没有险峻的山峰,我们说“go hiking”充其量也就是徒步。秋日去看“ruska”,这个芬兰词汇指“山林渐染秋意的千万种色彩”,芬兰中部和北边的国家森林公园是此时的好去处。冬日(十一、十二月),是天色最黯淡、最让人厌倦的月份,休假的话,大都会选择温暖的南欧补给点光和热;不过一二月则是在拉普兰(Lapland)观赏极光的好时机, “滑雪跨年”也算是常见的消遣。 Continue reading
-
喜闻乐见
脸小的人画浓妆,面面俱到地涂了粉底、高光、修容液和腮红。偏橘红色的粉从眼梢扑到颧骨上,而颧骨和下颌间浅浅的山谷里又匀净地刷了一笔浅棕的修容液。定妆喷雾一氤氲,这暖色的腮红同浅棕的阴影便粘稠起来,二者朦朦胧胧地一过渡、一勾兑,照着寻常日光,真是泥土的颜色。每每看到有如此妆容的女士,心里都会浮现”面如土色“这个词语。 Continue reading


